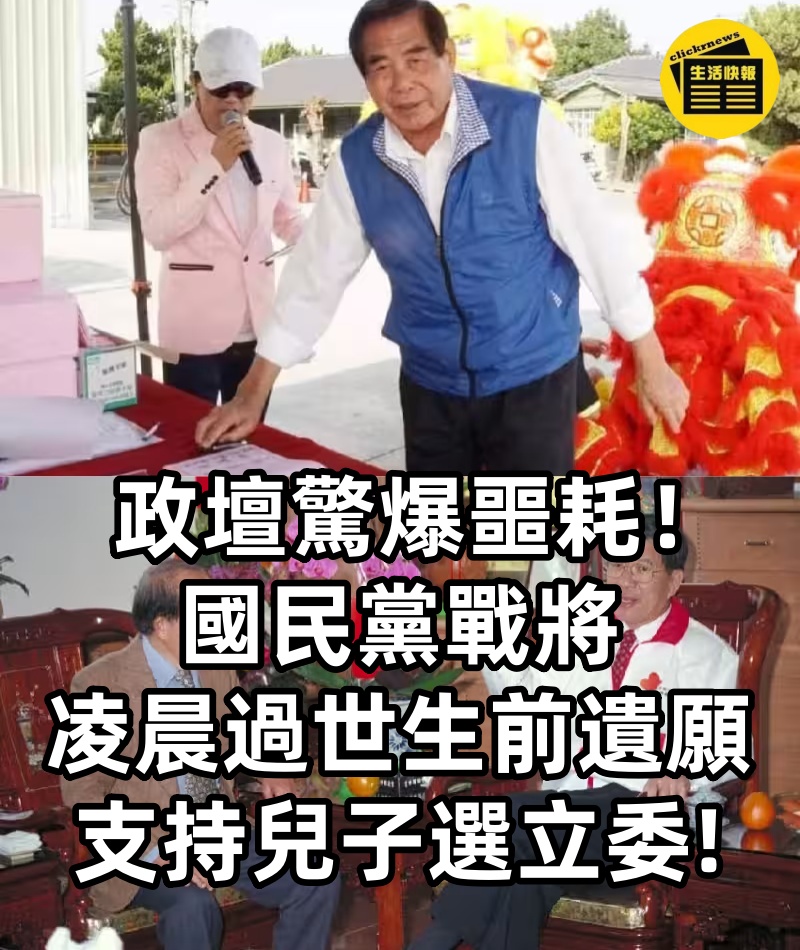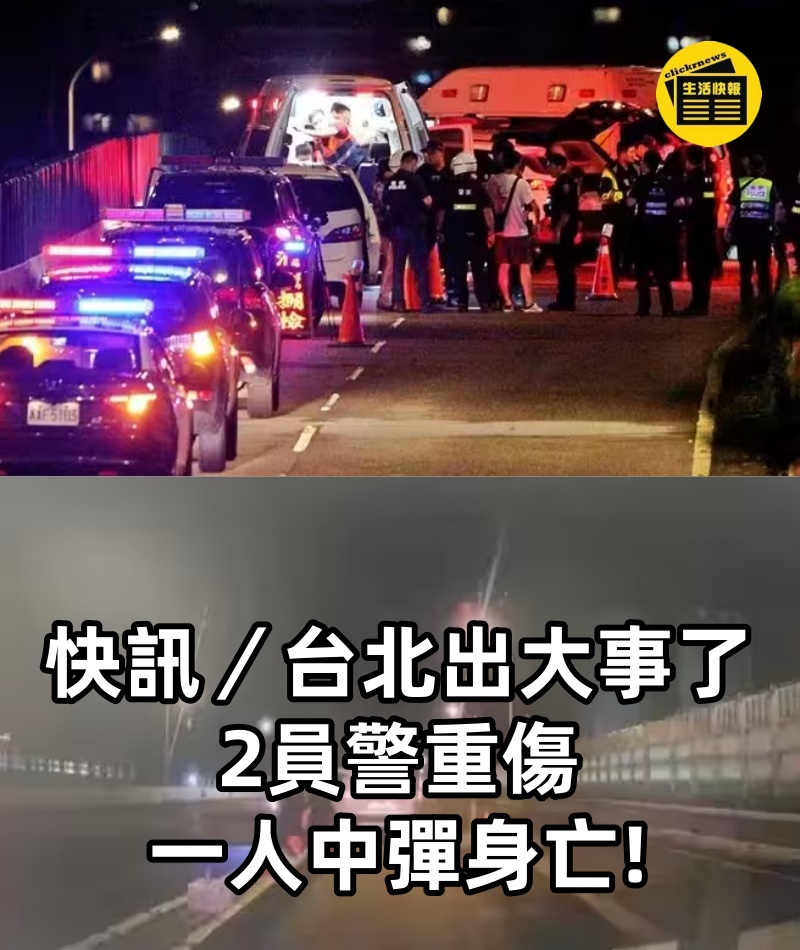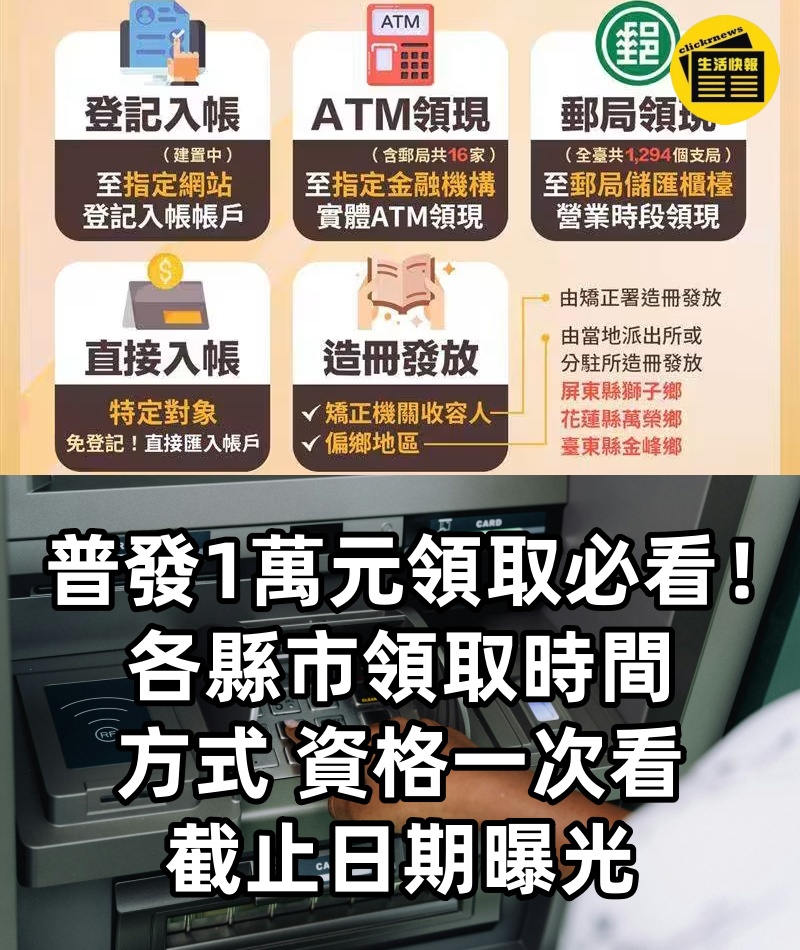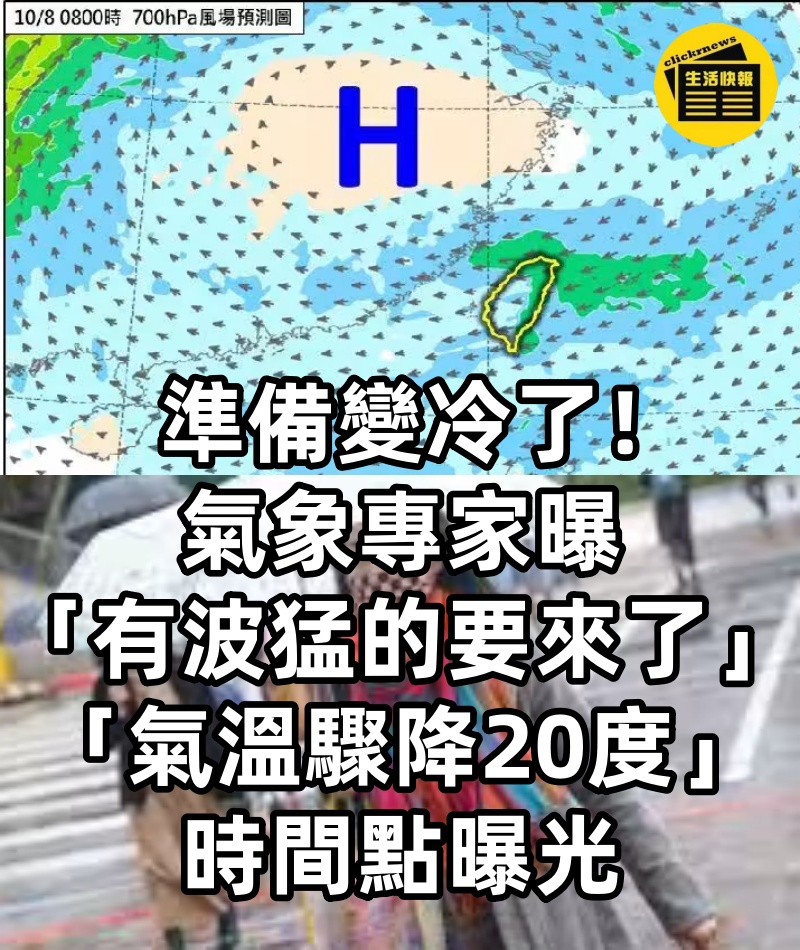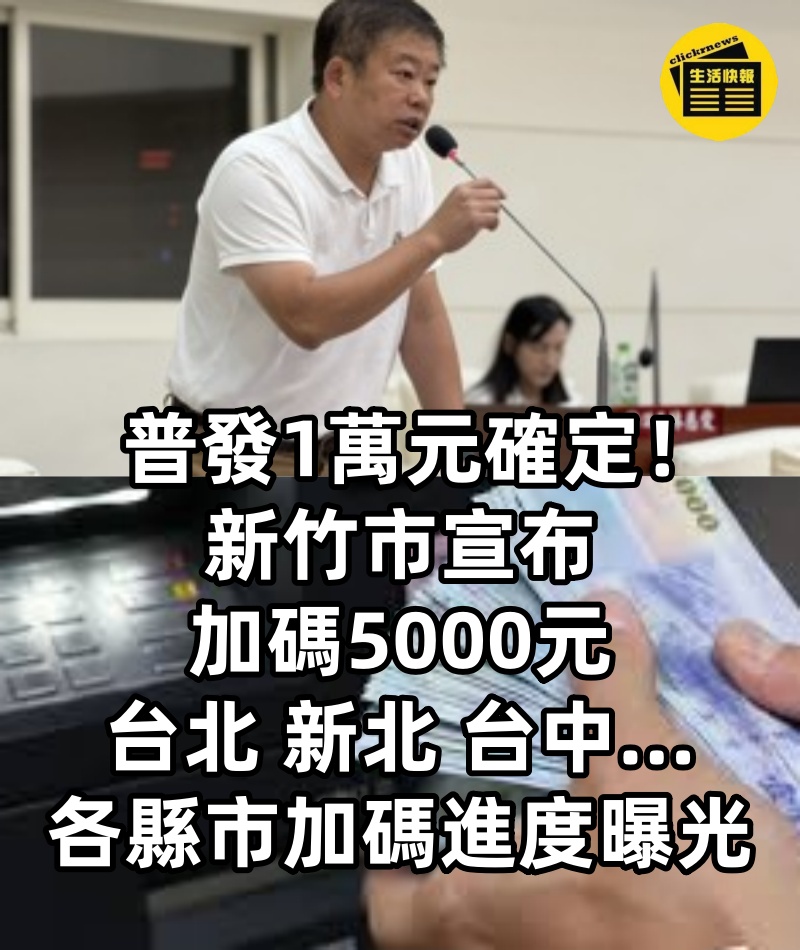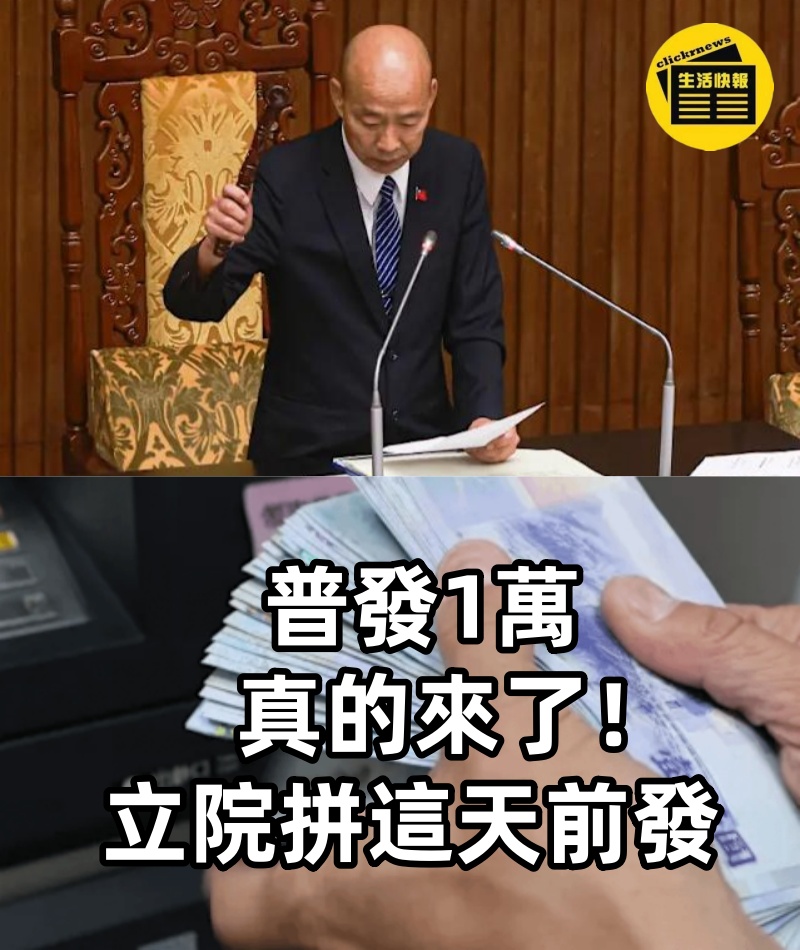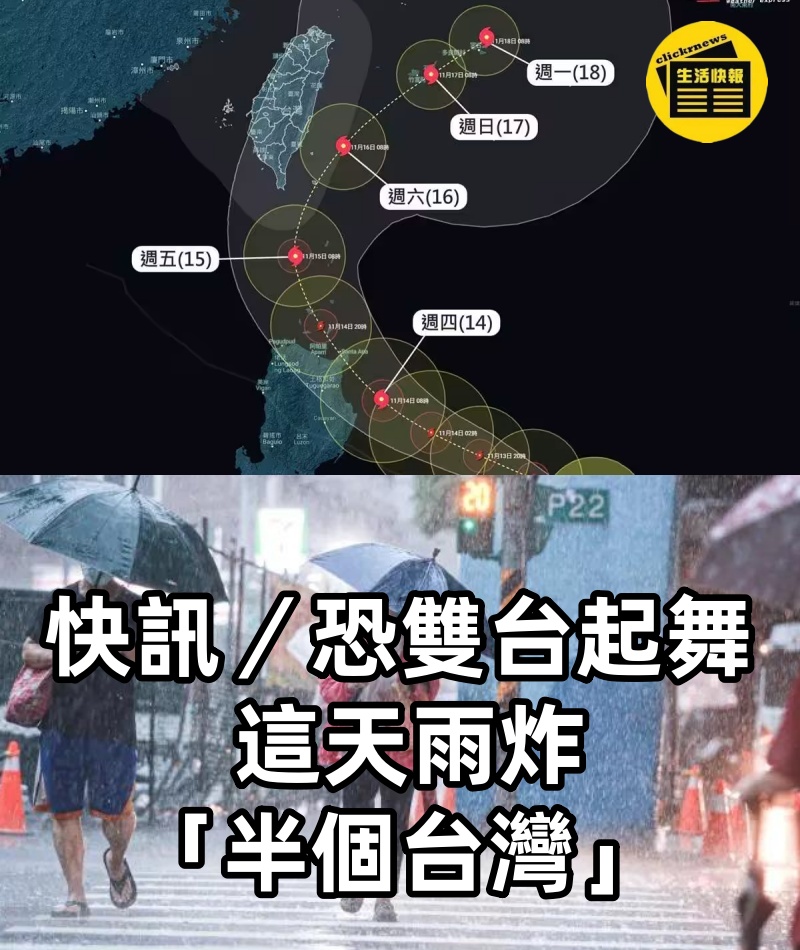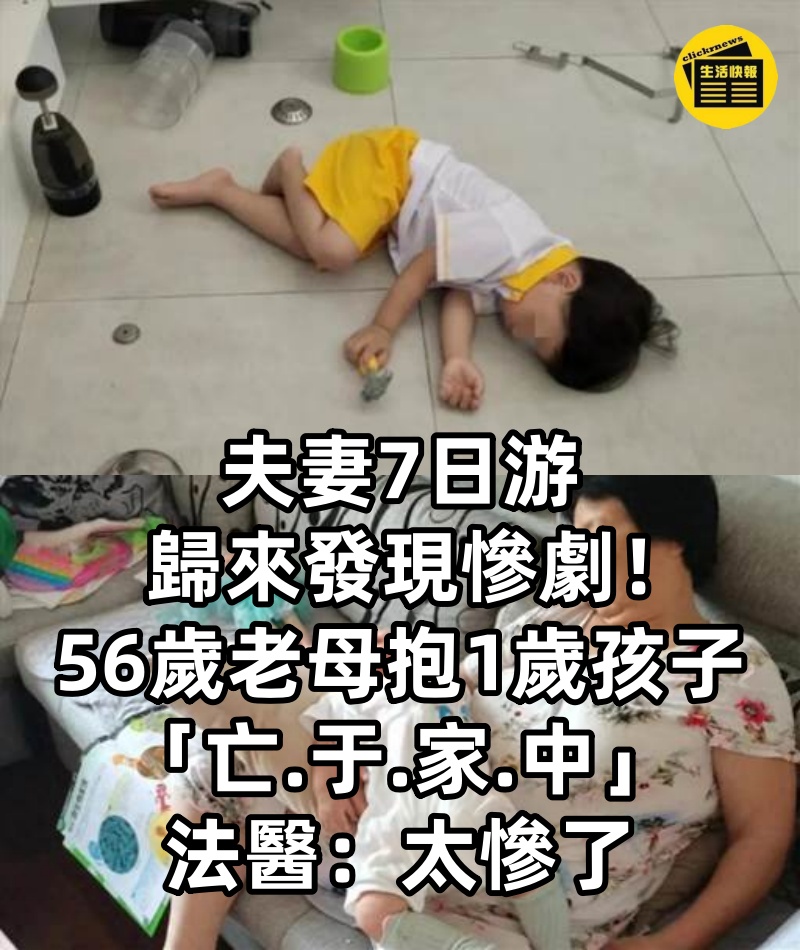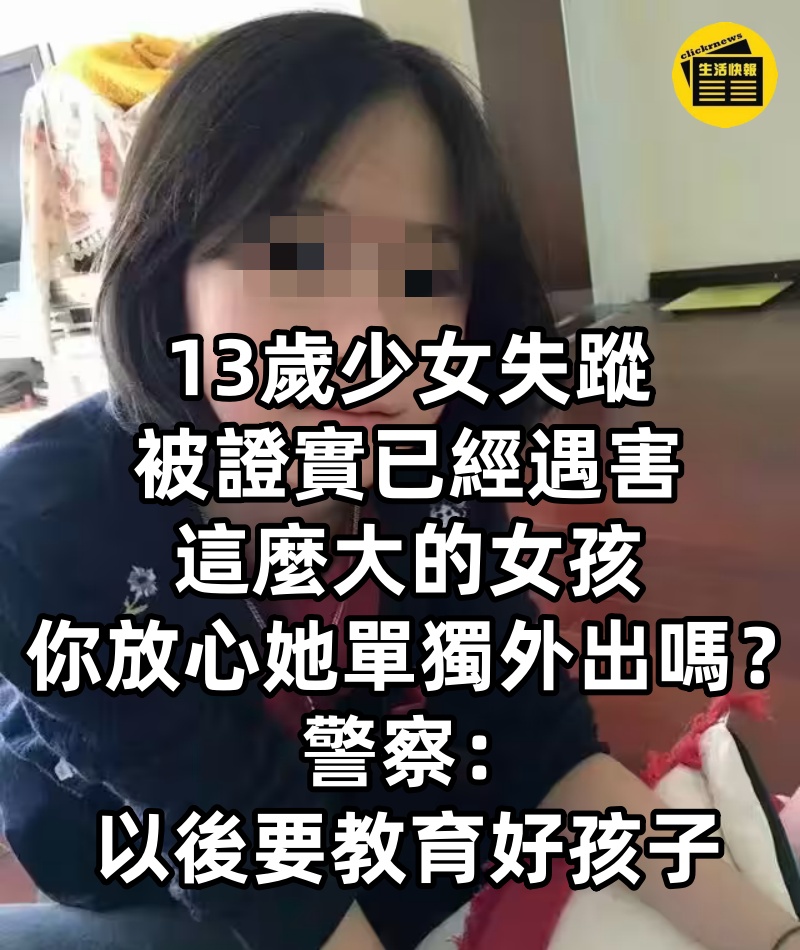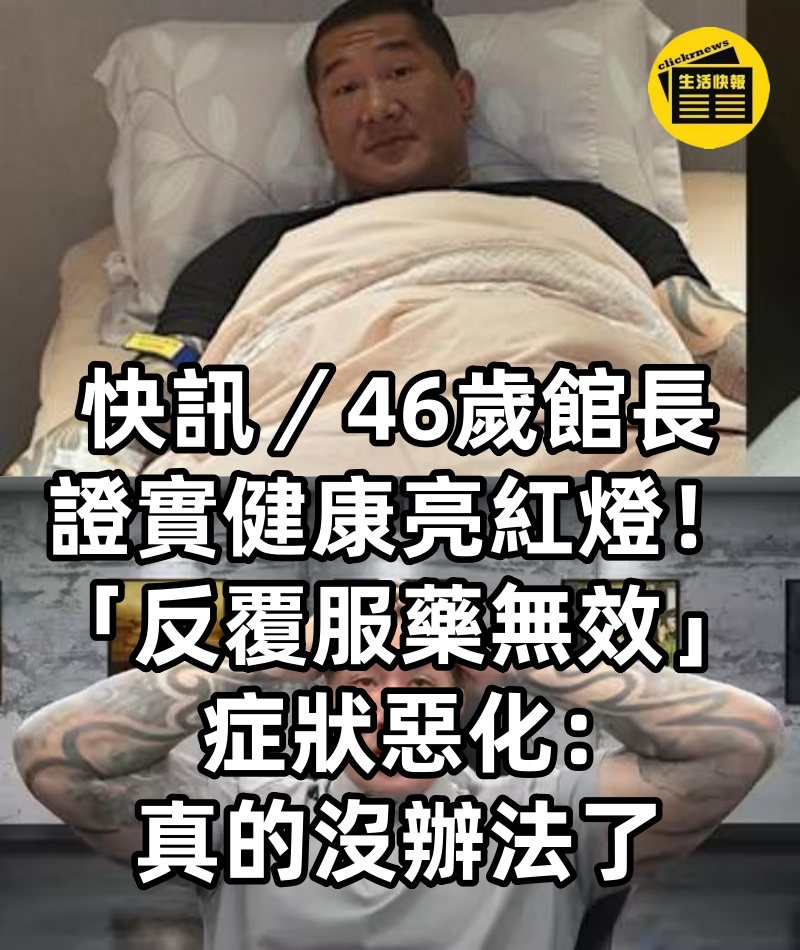台灣殯儀師工作20年,終於不堪重負,首次曝光人死後火化的全過程!太痛苦了,看完沒有不哭的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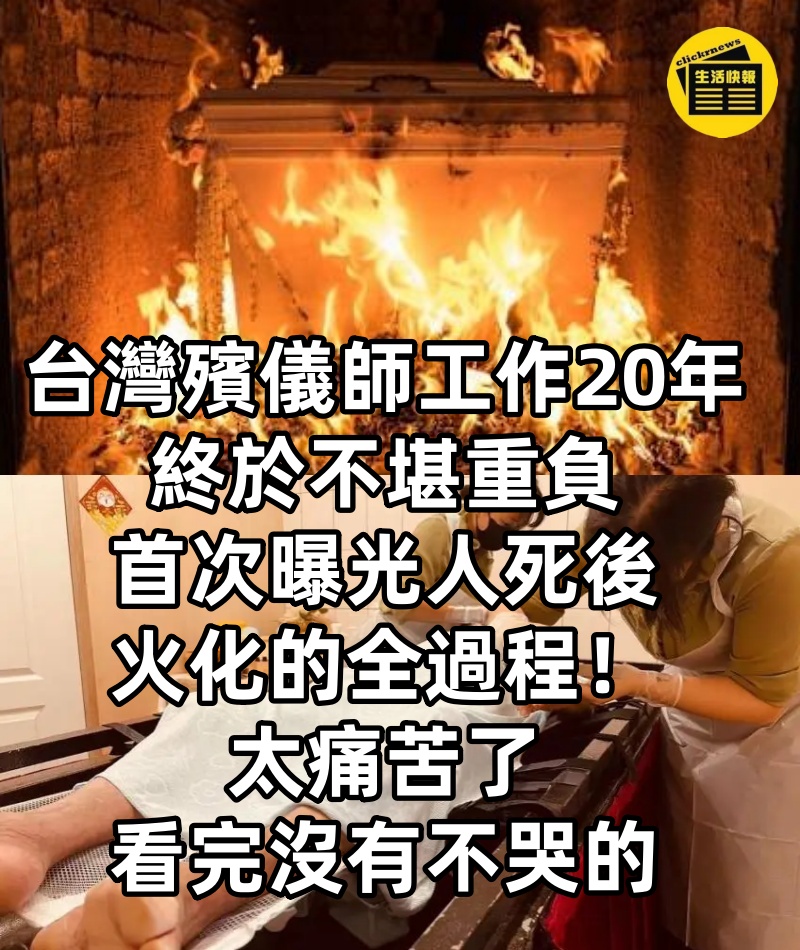
對死亡的忌諱幾乎是刻在中國人的骨子裡,平時你要是說了一句“死”,指定要被家裡老人抓住連喊幾句呸呸呸
許多公寓大樓和大樓也因此在樓層上都會避免4、14、24的數字,彷彿只要與死亡掛鉤的東西,那都是晦氣的。
但就有這麼多女孩,19歲就踏入了一個被大多數人避諱的行業-殯葬。
工作期間她不只要面對生離死別的悲傷,還要接受親戚朋友異樣的眼光,但即使如此她也堅持了下去,這一干就是20年。
究竟是什麼讓她堅持在這個備受偏見的行業堅持20年?

19歲入行殯葬
2002年,李曉婷只有19歲 ,剛從學校畢業的她選擇了一個與大多數年輕人不同的道路-進入蚌埠市殯儀館工作。
她知道做這份工作不僅要客服對死亡的恐懼,還要面對外界的偏見。
每次提起自己的職業,親戚朋友投來的眼神裡都有一種莫名的異樣和避諱。

尤其是她的父母,雖然他們尊重她的選擇,但也不免感到失望和不解。
不過剛開始進入殯儀館時,李雪婷幾乎沒有時間去思考這些,因為她的每一天都忙得不可開交。
身為殯儀服務員,她的工作繁瑣而細緻,從遺體的接收、整理到告別儀式的策劃與主持,每一項任務都需要極高的責任感。

儘管對許多人來說,和屍體打交道是一種無法忍受的事。
但李曉婷漸漸明白了,這份工作所需要的不僅是堅強的心理素質,更多的是對逝者和生者的尊重。
每天早上7點半,李曉婷準時走進告別廳,換上乾淨整齊的製服,開始為逝者主持告別儀式。

告別逝者敬畏生命
一場儀式通常只有半小時,但在這短短的時間裡,她要完成一系列環節,從介紹逝者的生平、家屬默哀,到讓親屬向遺體 告別,每個步驟都需要精準到位。
許多遺體由於意外或長期病痛,面容或多或少都有些損傷,李曉婷和她的團隊需要花時間進行修復和美容,以便給逝者一個體面的離開。
每一場儀式前,李曉婷都會親自檢查遺體的狀態,如果需要修復,她會和同事們一起,細心地修補破損的部分。

她記得有一位年輕的烈士,由於長時間浸泡在水中,臉孔幾乎無法辨認。
為了讓殉道者 有一個體面的告別, 李曉婷和她的同事們花了整整十個小時 ,為他做了遺體修復和化妝。
在烈士的面容恢復後,李曉婷內心感到無比的滿足,因為她知道,這樣的修復不僅是對殉道者的尊重,也是對家屬的一種安慰。

隨著時間的推移,李曉婷不僅在工作上累積了豐富的經驗,還逐漸意識到,自己之所以能在這個行業中堅持這麼多年,是因為她找到了這份工作背後的深層意義。
她不再只是把它看作一份工作,更多的是看到自己為逝者和家屬所做的貢獻。
在她看來,每一場告別儀式,都是一次生命的禮贊,雖然死亡不可避免,但每一位逝者都應該得到尊重,家屬也應該有機會在儀式中找到安慰與釋懷。

這份工作雖然忙碌,但每一場儀式結束時,李曉婷都會覺得心裡充實。
入行20年無愧於心
她記得曾經有一位母親,在告別儀式後,緊緊握住她的手,感謝她帶了孩子最後的尊嚴。
李曉婷沒有多說話,只是輕輕點頭,她知道自己做的這一切,最後都是為了幫助家屬平復心中的痛苦。

即便這份工作常常讓她感到疲憊,但每當她看到家屬的淚水中夾雜著感激,她的內心就會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滿足。
在這些年的工作中,李曉婷也與她的同事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,她們在工作中如同姐妹一般,互相支持,互相照應。
她所在的團隊被人們親切地稱為“七仙女”,這個名字的由來很簡單,因為她們總是以溫柔的態度對待每一位逝者和家屬。

不管工作再忙,她們的心中總有一份堅定的信念,為死者送去最後的尊嚴,為生者帶去一份安慰。
李曉婷和她的團隊並不孤單,她們的付出逐漸得到了社會的認可,隨著時代的發展,人們對殯葬業的看法也開始改變。
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理解並尊重這一行業,而李曉婷和她的同事們,也透過自己的專業和努力,讓更多人意識到,死亡並不可怕,告別也不一定是終點。

20年過去了,李曉婷依然堅守在這個崗位上,每年5000場告別儀式,成了她工作的一部分。
每天的工作充實而忙碌,但她從未覺得疲倦,相反她總是從每一場儀式中找到自己的動力,這份工作值得她為之奮鬥一生。
「哭靈人」李美珍
在殯儀館工作的李曉婷尚且不能被人理解,李美珍作為一個「哭靈人」 更不為常人所理解,她以淚水換取金錢,幫助家屬送別親人。

這份工作最開始是李美珍不得已的選擇,她出生在福建的一個貧困家庭,早年輟學做農活,18歲時被父母安排嫁給了鄰村的男人。
婚後的生活與她的期待截然不同,丈夫無所事事且暴力成性,李美珍忍受了許多年的折磨。
直到有一天,她在葬禮上看到一個「哭靈」女人,深深觸動了她,她意識到或許這是她改變生活的機會。

雖然「哭靈」是個被許多人視為「晦氣」的行業,李美珍並不在乎外界的眼光。
她決定投身其中,藉此機會獲得經濟獨立,擺脫丈夫的束縛,為孩子們提供更好的生活。
沒有人教她,她只能自己摸索,參加不同的葬禮 ,觀察其他「哭靈人」的表現,漸漸培養出了自己的「哭功」。

每次參加葬禮,她都事先了解逝者的生平,用真摯的情感來表現悲傷。
第一次拿到70元報酬時,她感到無比的滿足,那是她人生中第一次的「眼淚變成的收入」。
在接下來的22年裡,李美珍參加了近2,000場葬禮,她的收入從最初的幾十元漲到今天的3,000元一場。

她常常一整天從葬禮跑到葬禮,疲憊不堪,但她從不抱怨,每一場葬禮,都是一個故事,承載著生命的終結與生者的痛苦。
李美珍在無數個送別 的瞬間感受到生命的脆弱與珍貴,慢慢地她對死亡的看法變得更加淡然。
如今她的兩個兒子也都成年,過著了穩定的生活,但李美珍依舊默默堅守在這個別人無法理解的崗位上。

我是老吳,30歲,是遺體美容師。
我進入這個行業已經11年了,從青春年少走到了中年。
我的工作就是洗去逝者一生辛勞,洗淨逝者苦痛的肉體,安撫悲傷的家人,讓逝者向這個世界做體面的道別。
這十幾年,我見過生死,見過離別。這也讓我懂得,我們要對身邊的一切充滿感恩,眼中有愛,心中才有愛,生活才有愛!
(我和同事在溝通工作)
90年代,我出生在台北鄉下的一個山村。家裡有爺爺奶奶,爸爸媽媽、我和哥哥。
小時候,我生活得非常辛苦,我想特別說一下,我說的辛苦不是普通的辛苦。
我們家的經濟狀況很差,爸爸還有家暴問題,他和媽媽都沒有在照顧家庭,我是在爺爺奶奶的身邊長大的。
爸爸是爺爺奶奶最小的小孩,所以,我小時候,他們已經八十好幾歲,沒有了工作賺錢的能力。
那家需要開支,需要吃的穿的,怎麼辦?只得我從小就出去工作哦。
我從國小四、五年級開始,就去餐廳打工,幫人家打包便當盒。除了可以賺工資,還可以打包一些飯菜帶給家裡的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