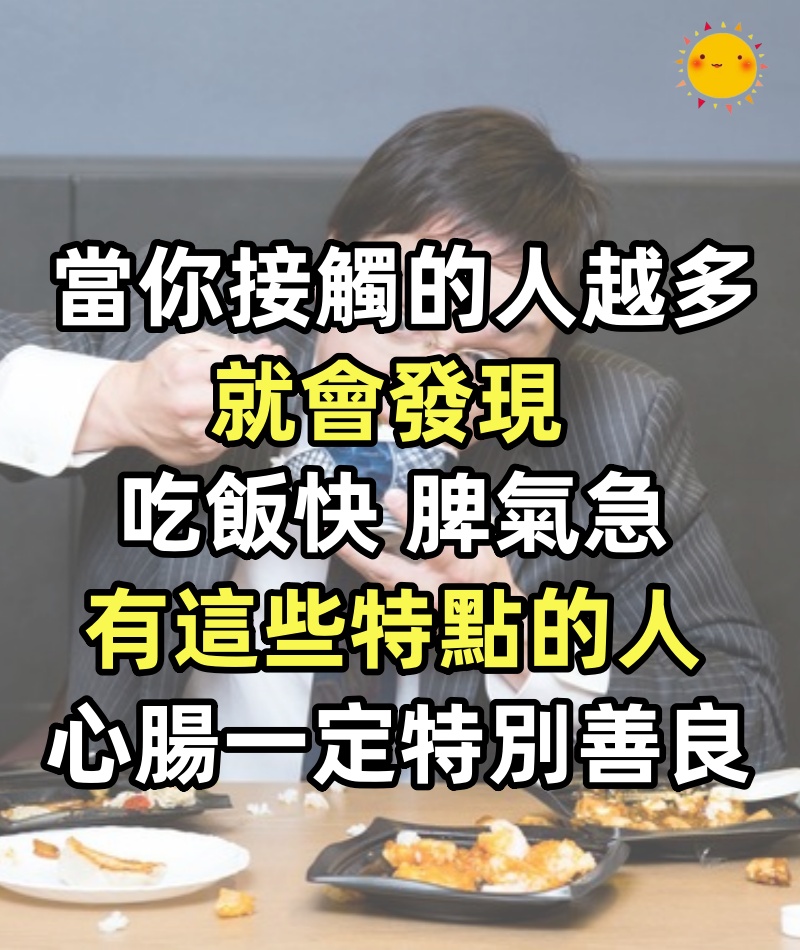兒子都上大學,買了房子,可是我跟老伴還是住進了養老院!

因為彼此無擾,我們和孩子們的關係處理得非常融洽。但是,不到10年,計畫就全被打亂了。
我們沒有料到,自己的身體會垮得這麼快。

怎麼辦?只有終止雲遊四方的日子了,提前進入請保姆的程式。
可是,真的開始請保姆時,我們才發現自己太幼稚了。
我們最先找了家政公司,伺候兩個老人,對方給出的要價是每月3000元。
這個數目雖然也在我們能承受的範圍內,但還是讓我們有些小小的驚訝。
我們研究所剛剛畢業的研究生,一個月的工資也就是3000元。
可是一個不用受太多教育就能勝任的保姆崗位,也開出了和一個研究人員同等的薪酬標準。
但我們處在供不應求的市場環境中,
只能接受如此的定價。
當我好不容易把老伴兒的思想工作做通了,
將第一個小保姆請進了家門後,卻發現服務品質和我們的預期完全不相吻合。
我們老兩口也是自認有修養的人,但是的確難以容忍。
於是換了一個,每個月還多給出500塊錢。
但是,付出的價格逐漸抬高,獲得的服務品質與預期的落差反而更大了。
就這樣接二連三換了4個保姆,最終不約而同,我和老伴兒都決定不再嘗試這條路了。
我們決定,在我們還能動的情況下,彼此照顧對方。

違心的理性思考。
我們都是學理科出身的,不會感情用事。
任何決定,都是經過理性推理出來的。
但是現在不得不承認,
我們的理性思考的確有僥倖的成分在裡面。
就說老年人的身體狀況,完全存在不可估算的變數。
上次突發的身體危機,讓我們產生了一個共識:
住院兩個人必須一同去。至少我們最終的那個時刻,
會是雙雙躺在醫院的病床上,彼此看得見對方,一同閉上眼睛。
如果真是這樣,那可的確就算功德圓滿了。
但,孩子們並不能理解我們。他們總以為我們是捨不得花錢請保姆。
他們不知道,即使捨得花大價錢請了保姆,也依然換不來等值的服務。
我們住院後,兩個孩子都回來了。
以前我可能覺得,他們用不著回來,回來也不能改變我們需要救治的事實,
也給不出更好的解決方案。但是,這一次我不這麼認為了。
當孩子們出現在病房門口的時候,那一刻,我真的感受到了情感上的滿足。
那一刻,我居然有些傷心,就好像自己受了什麼天大的委屈一樣。
老伴兒更是哭得一塌糊塗,孩子們越安慰,她哭得越凶。
孩子們難以理解,他們的父母怎麼會變得如此脆弱,
就像我年輕的時候一樣,也一定是難以理解如今的自己。

孩子們在醫院陪了我們幾天,
看我們的病情都穩定下來了,就回北京了。
他們太忙,是我讓他們回去的。
有生以來第一次,我在理性思考的時候感到這麼違心。
暮年的最後一站。
在醫院裡,我和老伴兒做了一個決定
——我們住進養老院去。
因為養老院畢竟是有組織的管理,
可以杜絕「老人在家養老,保姆關起門來稱王稱霸」的可能。
我們看中的那家養老院,提供家庭式公寓,每天服務員會送來三餐。
自己願意的話,也可以自己做飯。
醫務人員會隨時巡視老人的身體狀況。
這家養老院的公寓房很緊張,需要排隊。
我們辦好了入院手續後,等待著養老院的通知。
去養老院,應該是我和老伴兒的最後一站了。
也許真的是走到人生的盡頭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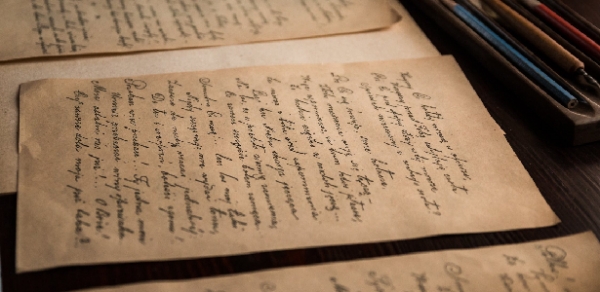
這段日子在家,
除了收拾要拿到養老院的東西,
每天夕陽落山的時候,
我們老兩口就坐在陽臺上聊起過去的事情,像是在告別。
前兩天,我和老伴兒做了一個大工程,
就是把孩子們從前的照片都整理了出來,
分門別類,按照年代的順序掃描進電腦裡,給他們做成了電子相冊。
我還買了兩台平板電腦,分別給他們把照片儲存了進去。
我們這一輩子,傳統觀念不是很重,自認為我們的生命和孩子們的生命應當是各自獨立的。
可是如今看來,人之暮年,
對於親情的渴望卻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。老伴兒現在特別思念孩子們,我也一樣。
這些日子,總是突然想起兩個兒子小時候的樣子。
有時候還會有些錯覺,好像看到他們就在我們跟前玩耍。
離開家時,我和老伴兒仔細想了想,要從這個家帶走的,好像並不需要太多的東西。
除了我們的養老金卡、身份證件,唯一值得我們帶在身邊的,就只有孩子們的照片了。

人生前一個階段積累下的一切有形的事物,我們都帶不走,也不需要帶走了。
看了李老夫婦的故事,其實覺得挺可悲的。
我們以為父母可以照顧自己,
但其實他們已經漸漸失去自己生活的能力,到了需要依賴你的時候。
而我們一直躲在他們的屋簷下避雨,如今自己已經到了要成為屋簷的時候了。
多回家陪陪父母吧。
與其出門在外見千千萬萬人,不如回家看看你最珍貴的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