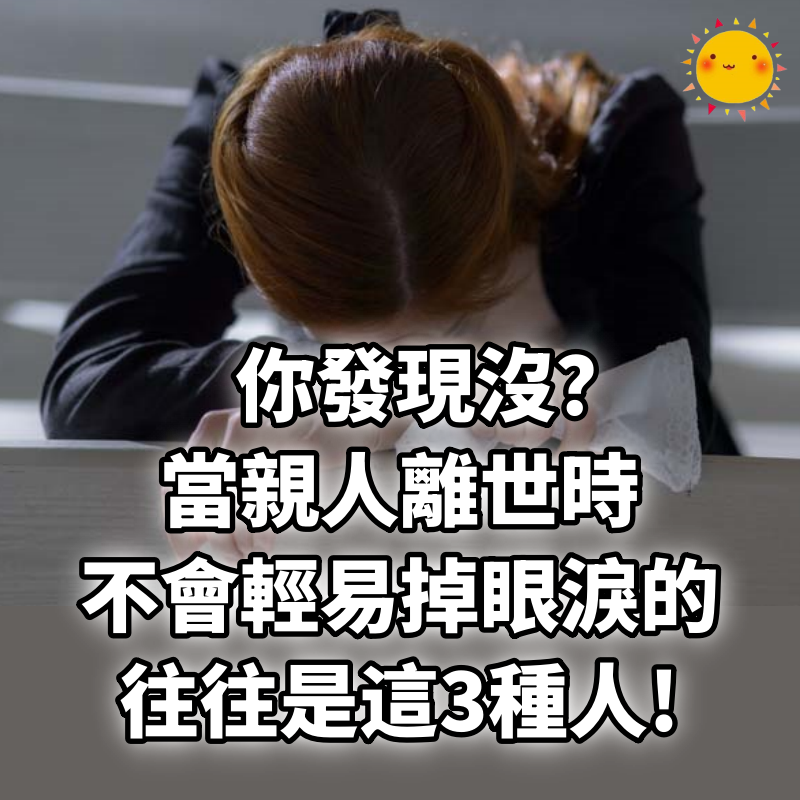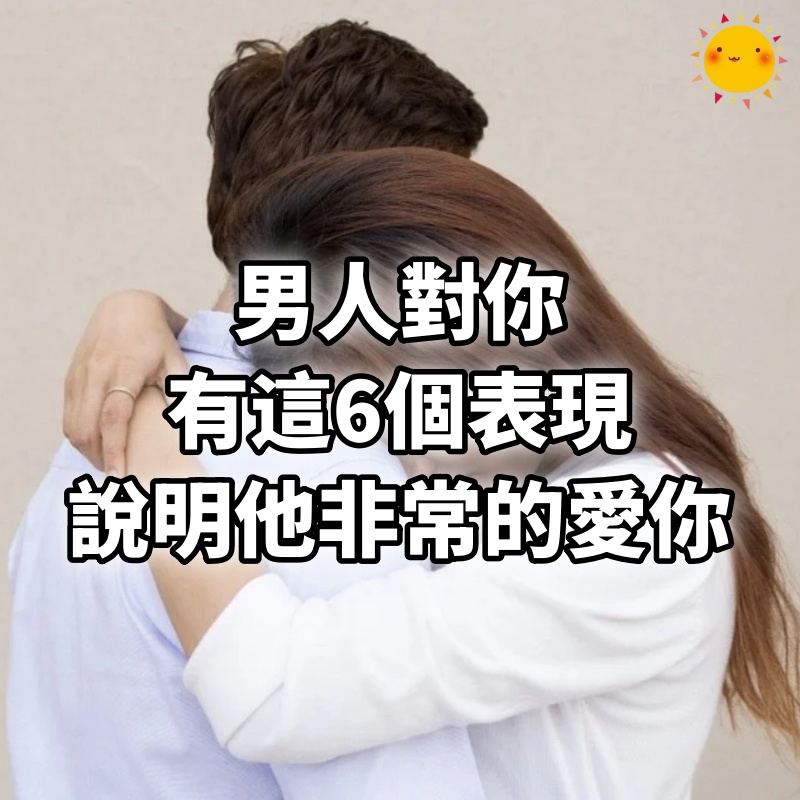原來臨終前是如此,懂了以後就別再帶給親人痛苦了!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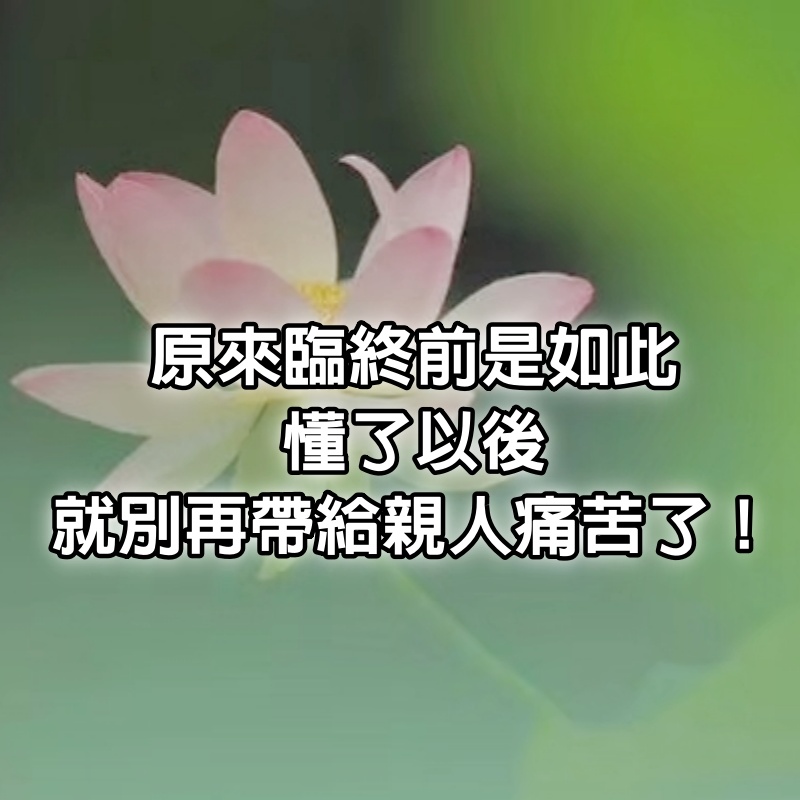
不過病人並不一定有痛苦,此時可用一些止痛劑,
使他能繼續與家屬交談或安靜的走向去世。
聽覺是最後消失的感覺,所以,不想讓病人聽到的話即使在最後也不該隨便說出口。

這幾天,我一再的說,我一再的想:
為什麼,為什麼直到現在,我才讀到了這篇文章。
現在是什麼意思?
現在是,我的父母已經先後去世,而一直到他們生命的最後時光,
我都沒有和這篇文章相遇,所以在無知中鑄成大錯...
所有的誤解都基於一個前提,我們和臨終者已經無法溝通,
我們最愛的親人已經無法講出他們的心願和需求,
我們只好一意孤行。
而本來只需要一點點基本的醫學常識,事情並不複雜。

我想起我抓著父親的手,他像水一樣涼。
我命令弟弟說:「爸爸冷,快拿毯子!」
現在才知道,他其實並不冷,只是因為循環的血液量銳減,
皮膚才變得又濕又冷。
而此時在他的感覺中,他的身體正在變輕,
漸漸的漂浮、飛升...這時候哪怕是一條絲巾,
都會讓他感覺到無法忍受的重量,更何況是一條毯子?
我想起直到父親嚥下最後一口氣,
醫生才拔下了接在他身體上的所有的管子,
同時因為我們覺得他幾天幾夜沒喝水、進食,
所已總是試著做一些哪怕是徒勞無功的嘗試。
母親早上送來現榨的西瓜汁,裝在有刻度的嬰兒奶瓶裡;
我們姐弟每天都在討論著爸爸今天到底喝了多少水。
現在才知道,他其實並不餓。

那時候,他已從病痛中解脫出來,
天很藍、風很輕、樹很綠、花很鮮豔、水在流,
就像藝術、宗教中描述的那樣……
這時候,哪怕是幫病人注射一點點的葡萄糖,
都會抵消那種異常的愉快感,都會破壞他美麗的歸途。
父親是個沉默寡言的人,在最後急性意識模糊的狀態中,卻突然變得喋喋不休,而且是滿口的台語。
我擔心他離我而去,我想喊住他,他卻絲毫不理會...
現在才知道,那個時刻,他與外界的交流少了,
心靈深處的活動卻異常活躍,也許青春,也許童趣,好戲正在一幕幕的上演。
我怎麼可以無端打斷他,將他拖回這個慘痛的現實中呢?
我應該做的,只是靜靜的守著他,千萬千萬不要走開。
臨終者昏迷再深,也會有片刻的清醒,這大概就是傳說的迴光返照吧,
這時候,他必定想找他最牽腸掛肚的人,不能讓他失望的離開。

我還記得父親此生表達的最後願望,
是要拔去他鼻子上的氧氣管。
可是我們兩個不孝子女是怎樣的違拗了他的意願啊,
我和弟弟一人一邊強按住他的手,直到他的手徹底綿軟。
現在才知道,對於臨終者,
最大的仁慈和人道是避免不適當的、創傷性的治療。
不分青紅皂白地「不惜一切代價」搶救,
是多麼的愚蠢和殘忍!
父親走了...
醫生下了定論,護士過來作了最後的處理。
一旁看熱鬧的病人和家屬說:
「兒子、女兒都在,快哭,快喊幾聲嘛」。
可不知為什麼,我竟然一點也哭喊不出來,
弟弟也執拗的沉默著。
現在才知道,聽覺是人最後消失的感覺,
爸爸沒有聽到我們的哭泣,不知道他是高興還是難過?
生和亡都是自然現象,這我明白。
只是現在才知道,
自然竟然把生命的最後時光安排得這樣有人情味,這樣合理,這樣好,這樣的...
自然而然,是人自作聰明的橫加干涉,去世的過程才變得痛苦而又漫長。

某一天上午,我突然發現我對面的同事淚流滿面,
一個50多歲的男人的失態讓我詫異。
問他怎麼了,他告訴我看了上面的文章想起了他母親臨終前的情形。
他說就像上文描述的那樣,覺得母親冷了給她穿保暖的衣服,
蓋厚厚的被子,覺得母親幾天沒有進食,不停給她輸液,他母親想回家,可他堅持讓她住在醫院。

他自認為盡了孝心,可是沒想到給她帶來莫大的痛苦。
人總是要沒的,帶著輕鬆、美麗踏進另一個世界,一定會走得更好。